| 中国新闻社主办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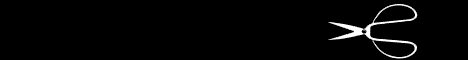 |
| |
张闻天庐山冤案与康生 2001年3月14日 10:37 作者 张培森(北京) 在延安就有过一段争论 众所周知,在延安整风审干中,康生有个“发明”,叫做“抢救运动”,整了一大批人,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当时住在他家隔壁的张闻天曾为此同他发生过一场激烈争论,对康生把那么多干部,特别是来延安的知识青年整成“特务”,张闻天很有意见,当面问他,知识分子中哪来这么多特务?向他严肃指出:这些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是为追求真理而来的,有些人社会关系复杂一些,但社会关系复杂并不等于他本人就有问题,而正好说明他们是“叛逆者”。康生当时拿来所谓“防奸经验”材料,张闻天看后明确表示不相信,说这里面可以看出许多是假的,是被逼出来的,而康生则硬说是真的。 经过一番争辩,张闻天知道跟他说不通,便把个人的意见反映给了任弼时,这样后来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才得以制止。这件事自然康生记恨在心。 凑巧的是,五十年代北京景山后街住着毗邻的两户党的高级干部,这两户的主人一位是历史上曾任党的总书记、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张闻天;而另一位就是当年在延安倚仗权势大搞“抢救运动”、解放后长期“养病”的康生。两家虽然一墙之隔,却很少往来。起初由于不同的历史原因,他们两人在党的八大上都从中央政治局委员降为候补委员。可是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两人的命运却大不一样。张闻天因在会上直言“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被打成“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沉冤十多年直至去世;康生则因善于投机、耍弄阴谋,而再次攫取高位,最后升至中央常委、党中央副主席。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四十多年过去了,张闻天不仅早已得到中央平反,而且愈加受到人民敬仰爱戴;而康生则是死后被开除党籍,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现在查明,张闻天的冤案固然与毛泽东晚年错误有关,而康生在其间的推波助澜,也是冤案升级的重要因素。康生捏造“郭肇唐事件” 康生的东山再起,是与他在庐山会议及会后整彭张的积极表现分不开的。张闻天冤案所列“罪行”中最荒唐的一条是:“里通外国”,这是一条完全莫须有的罪状。然而为了给这个罪状提供“证据”,康生竟然无中生有造出一个所谓同“苏修”勾结的“郭肇唐事件”。 郭肇唐是谁?他原本是中共的早期党员。张闻天很早就与其相识,后来在苏联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时二人又成为同窗学友,与王稼祥、沈泽民一起被人们誉为“四大教授”。学成后不久,张闻天回到国内,郭则留下,成了苏联公民。郭在三十年代苏联肃反扩大化中遭到迫害,被送至西伯利亚服苦役十多年,斯大林逝世后才获释放,被安排在苏联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当研究员。 1957年周总理访问苏联,郭当面向总理提出想回到祖国看看,总理当即表示欢迎。经过国内的正式邀请,郭于1957年、1958年先后两次来华,均受到热情接待,和郭二三十年代在苏联有过交往的老朋友、老同学都纷纷前来相聚,畅谈过去,共叙友情,张闻天也不例外。 而郭和张最初的会晤恰巧是经过康生引见的,因为康生过去在列宁学院学习时郭肇唐是他的老师,郭这次访问先看望了康生,康生还送给老师两只浙江金华火腿。谈话中郭提出还要去看望老同学张闻天,康便告诉他张就住在隔壁,并主动将郭带到张闻天的家中。 从这以后张闻天同这位老同学就恢复了交往。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后来康生竟倒打一耙,在张闻天同郭的交往上大做文章,把它说成“里通外国”的罪证,强加到张闻天的头上。 整张闻天所谓“里通外国”罪,最初是庐山会议上捕风捉影提出来的,至于张同郭肇唐交往的追查,则是在庐山下来之后单独批张的外事会议上提出的,然而这时这也还只是作为几个嫌疑问题之一。而康生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最终导致立专案审查,则是到了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这时正是中苏关系全面恶化,党内重提阶级斗争大批所谓“翻案风”的紧张时期。 这次全会没有让张闻天出席,他只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预备会议,并在西南小组会上作了几次检讨发言。在9月12日小组会上发言时,张即对所谓“里通外国”问题有过一个表态的说明:“我曾向中央做过声明,我认为虽然这种怀疑是有原因的,但是没有根据的,并要求中央长期考察我。”还表示:“我相信事情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 但是,在18日的小组会上,这个问题即遭到猛烈围攻,而康生正是扮演了这场围攻的主角,他专门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和质问就至少有4次。为了给张闻天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他先神乎其神地把郭肇唐说成是从来华访问开始就是一个专搞情报的“间谍”,断定他研究中国问题和来中国的目的都是为了搞情报,因为郭是赫鲁晓夫领导下释放的,因此他一定要给赫报恩;同时他又把他自己描绘得如何如何对这个“间谍”早就抱有高度警惕。然而很早就有人反映,郭肇唐来华后拿给一些国内同志看的一封中共高层的复函,恰恰就是康生的亲笔,其中清楚地写道:我们知道你的情况,对你是信任的。 当时康生抓住张闻天的一个所谓“要害”问题,是说张闻天将党内的文件送给了郭肇唐看。这在当时被说得煞有介事,然而这件事究竟真相如何?事实是:郭在1957年第一次访华,了解一些中国国内情况后,认为苏联许多人都对中国并不真正了解,为了正确地了解中国、宣传中国,他对张闻天说,他过去是中共党员,现在又在研究中国问题,想要了解一些党的政策,能否让他看一些中国普通党员能看的党内文件。那时还是中苏关系友好的时期,两党中央有些内部材料是可以进行交换的。尽管如此,作为外事纪律,张闻天还是请示了上面,开始没有答复,也就没有给看。1958年第二次访华时郭又提出这个要求,张闻天再次作了请示,这次得到了上面批准,说可以试试。这样张闻天才通知了驻苏使馆给他看一些一般党员所能看的文件材料。 张闻天会上如实地陈述以上的事实经过之后,有的同志提出还要核查,而康生则立即狠批张闻天这是把责任往上面推,拿出一槌定案的口气说,“我肯定说这就是里通外国”,“我看里通外国的帽子戴得不错,戴得对。” 康生之所以抓住张闻天“里通外国”这个题目不放,显然离不开那个时候中苏发生分歧这个大背景,投好了上面以外压内的意图。1958年我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掀起以后,国际上反响很大,同时这也成为中苏的分歧之一。毛泽东庐山上8月2日给张闻天的那封信中开头就批张闻天,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那么多材料?这句话实际就暗示批他有同国际上反华活动串通的问题。 凑巧的是,庐山会议前彭德怀、张闻天差不多同一时间以不同的使命出使东欧,途经苏联,最初追查他们二人串通起来“里通外国”,即与此有关。 张闻天本人的回答是很坦然的,他在检讨中并不讳言他在“三面红旗”问题上有同苏共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和观点,但认为这绝不等于那种出卖党和国家的背叛行径。他在外事会议检讨中甚至说:如果说,在“思想观点上”苏共领导者和我之间“在反对党的总路线”这一点上有“共同点”,因而认为从政治思想上说我有“里通外国”的表现,那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说,在组织上,即情报关系上,我有“里通外国”的表现,那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根本没有这类事情。他也同样坦率承认,为了了解苏联对中国“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真实反应,在1959年同郭肇唐接触中确曾询问过有关情况,郭也确曾告诉他苏共领导对中国人民公社持保留态度,并说苏联真理报和哲学杂志上发表的学者文章,批评中国“大跃进”中宣传的有些观点是愚蠢的观点,然而这些当时在苏联也都并不是什么秘密。 对于庐山的冤案,最使张闻天感到冤屈的莫如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他曾经对身边的妻子刘英说,说我反对“三面红旗”,那毕竟是观点问题,说我“里通外国”,那简直是太冤枉了。刘英说,从来没有见他哭过,这一回见他眼泪直往下淌。 康生的得势与张闻天的沉冤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康生在整个庐山冤案的推进中是十分活跃的,庐山上他批斗彭张的发言,1962年的围攻逼问均有记录在案。为给这场批判提供理论根据,他在庐山风云骤变时奉呈的《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问题》语录备受赏识,毛泽东批发出席会议者人手一份。后来以康生个人署名的《共产党员应当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是党的同路人》文章的发表,更是给公开批判大造了声势。 康生当年如此活跃,所倚仗的主要就是假借毛泽东这面大旗,而他六十年代在党内的重新得势,也正是与他利用这面大旗取得一个又一个整人的辉煌“战果”直接有关。八届十中全会前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点出了批判“单干风”,康生就立即抓到了整邓子恢的一张“王牌”,即此前不久搞到手的邓子恢在中央党校的一篇讲话记录,邓在这篇讲话中直率地批评了“大跃进”时农村一些“左”的错误。这一下子老账新账一起算,又一个敢于讲真话干实事的老共产党人被击倒在地。毛泽东会上点出了批判“翻案风”,康生更是无中生有地抓住一部小说《刘志丹》,硬说它是为高岗翻案,是贬低毛主席创立的江西革命根据地。康生的一句话“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居然就造出了一个古今少有的奇案,不仅小说的作者蒙冤,而且被罗致“反党”罪名的,上自国家的副总理,下至该书的责任编辑,冤案十多年,波及人数尤为惊人。 对于张闻天,1962年抓不到任何“翻案”的证据,于是就旧账重提,抓住庐山会议上他自己坦率交待的“斯大林晚年”谈话,加上所谓“里通外国”问题,穷追猛打,最终立案审查。康生也就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且不久还当上了彭德怀张闻天专案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张闻天却从此坠入了深渊,取消中央政治局成员的一切待遇,不让参加一切中央会议和阅读所有中央文件,被迫无休止地检讨,交待那永远也交待不清的“反党”问题。 庐山风暴过后,张闻天被安排担任什么实际职务也没有的“特约研究员”,但他一颗赤诚为党为民之心始终未泯。就在1962年被宣布专案审查之前,为了探求解救当时中国经济困境之路,他还主动争取到一个去南方调查的权利。通过对江苏、上海等省市为期两个多月的社会调查,回京后写了一篇建议开放市场的报告《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报送中央,上报之前妻子刘英不无担忧:庐山的教训还不记取?劝他是否就不要往上送了。但张回答:“我是共产党员,既然看到了问题,该建议的还是要建议。” 到了“文革”,算起来张闻天最受磨难的一件事,也就是康生强迫要他为其阴谋制造的“六十一人叛徒”案提供伪证。当时给他造成的两难境地是:要么跟他们一起诬陷刘少奇,说过去中央不知道,是刘少奇背着中央干的;要么就如实地证明此事是经过当时中央批准的;如果是后者就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嫌。张闻天经过一番认真思考,毅然决定这件事由自己单独来承担:是我批准的,当时我是中央的总书记。 康生得知后大为恼火,在张送给他的一封信上批示:“张闻天又要玩弄骗人的把戏”,“应予以坚决回击”。但张闻天对康生派来的人说:“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 所谓“斯大林晚年”问题 庐山批判张闻天、彭德怀,被康生等人视为最大“战果”的是:彭、张都交待了他们在会下议论过毛泽东要防止斯大林晚年错误。这件事在当时是带有爆炸性的。 当时就有人批张是为了“推翻毛主席”,张虽然表明心迹“谁想推翻毛主席?就是真要推翻也推翻不了!”“大跃进的问题纠正也只能靠他”,但下山后接着分别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和外事会议,进一步追查的也仍是这件事情。到了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批所谓翻案风时,这件事更成了康生等拿来批判张闻天的重点、设立专案的根据。 下面这段对话同样出自1962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西南组会议记录,是康生批斗张闻天时关于所谓“斯大林晚年”的一段“质问”对话: 康生:你讲过毛主席与斯大林晚年一样,你为何要作这样的联系? 张闻天:我是说斯大林后期的错误要防止。我现在回想当时我讲这话的含义,基本上还是讲主席好,如说主席很英明,善于运用历史经验,说主席功劳大,威信高,同斯大林后期相同,但也说了主席的坏话,如说主席整人很厉害,主席对人也使用些“权术”,要防止斯大林后期的错误。 康生:你攻击主席“斯大林晚年”,这次你在发言中又轻描淡写。毛主席领导全国革命胜利,毛主席对中国人民这样大的功绩,你还用这样恶毒的字眼进行攻击,你反对毛主席,你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你是站在敌对的资产阶级立场的。 将近四十年后的今天,人们来看一看这两人在那种情况下的这段对话确实是耐人寻味的,它向人们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第一,这段对话首先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究竟谁对领袖人物真正负责? 现在看来,历史的遗憾是,当年不为人们所理解的张闻天关于“斯大林晚年”这番话,没有想到后来却成为一段不幸而言中的遗言。如果说毛泽东的错误毕竟是一个伟人犯下的错误的话;那么康生的媚上只不过表明他是一个历史上跳梁的小丑而已。这里昭示人们的一个真理是,不能把维护领袖的个人威信同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对立起来。 事实上,正是“大跃进”所暴露的严重问题,促使彭德怀张闻天不能不关注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并自然地同在此不久前苏联刚揭示出的斯大林晚年错误的深刻教训联系起来思索。早在上庐山之前,张闻天就曾不无隐忧地说:“斯大林后期威信确实很高,谁敢给他提意见?斯大林听不到反面意见,因此,犯了很大错误。当前国内是否也有这种情况呢?”而这种担忧正是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上发言的一个思想出发点。后来他虽被迫作了违心的检讨,但是痛苦的他,思想上一直想不通自己究竟错在哪里。 1962年他通过南方调查,更加坚定了原有的认识,回京后他对刘英说:庐山会议发言我并没有错,事实上那次所说的还不到千分之一呵! 然而对照之下,康生“大跃进”那几年干了些什么?这里必须指出,会上批斗张闻天的这位康生,当年正是“大跃进”的狂热鼓吹者。当时他以中央领导的身份到处视察,到处鼓吹“敢于胡搞就行”,甚至说“胡搞就是科学研究”;到处煽动:“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思想有粮就有粮,思想有钢就有钢”这类极端唯心主义的口号。可是康生不但庐山会议上没有挨着批评,而且反倒又搬出“大跃进”时鼓吹的夸大主观能动性的谬论,批判起张闻天庐山会议发言中所坚持的真正的唯物主义观点。实践证明,这种思想理论上的混乱,正是党在一个相当时期“左”的错误得不到彻底纠正、毛泽东个人也陷入更大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究竟是基于什么思考,促使张闻天产生对毛泽东“斯大林晚年”错误的忧虑? 张闻天在自己的“检讨”中有过这样的交待:“关于斯大林后期的问题,是从说毛泽东同志说了算、毛泽东同志不民主、集体领导等问题扯起来的。”彭、张二人当时都是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他们不约而同地都关注到党内民主这个问题,确实并非偶然。 实际上这两位在过去革命危急关头都坚决支持过毛泽东、并与毛泽东长期患难与共过来的老革命家,都早在庐山会议前就为党中央政治生活的日益不正常而忧心忡忡。其中最为触动他们的一件事,就是1958年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严厉批评“反冒进”,说反冒进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今后不要再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迫使周恩来进行检讨。 对这两次会议,彭德怀的反应是:“这种斗争方法,只注意建立个人威信,未注意集体威信。” 张闻天未能出席会议,但在听到南宁会议传达后也对会议那样的批判很有意见,认为“有冒进也要讲嘛”!及至“大跃进”掀起之后,面对到处盛行的浮夸风,张闻天更是感到问题的严重,于是在1959年春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专就民主问题发了言。 正是基于上述共同的思想,庐山上两位观点相同而又住得毗邻的老战友,便自然在深入交谈中倾吐了这番忧党忧民的肺腑之言。 事实证明,他们所说的民主问题确实是言中了,难怪张闻天在被迫第一次写检讨时,就边写边对秘书感叹地说:所以问题还是党内民主,这样以后还有谁敢讲话?! 一个值得总结的历史教训 康生这样一个人物究竟为何能在庐山会议后一个相当长时期那样得势?今天来看,分析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也仍然离不开张闻天所说的“斯大林晚年”问题。若论人物,康生是中共历史上一个带有典型性的值得总结研究的反面人物。别的不说,只就他打击干部、陷害忠良这一点来说,可以说是达到疯狂的地步。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十年浩劫”时期,经康生直接点名而被迫害的司局长以上的干部就超过千人,如果加上受株连的一般干部,则在万人以上。可是为什么就这样一个整人的恶神六七十年代竟在中央得势连续十多年之久,死时还被套上种种光环,直至1980年才被公开揭露出来开除党籍? 从康生本身来说,此人能在党内混迹那样久,最终爬到那样高的地位,自然也非等闲之辈,除了其革命资历之外,舞文弄墨,琴棋书画均有一点才能,但此人在政治上表现的最大特点是特别善于巴结领导,看风使舵。三十年代在莫斯科时他就肉麻地吹捧王明,差不多每次开会都要站起来呼喊“王明万岁”,可是延安整风时他批判王明却异常积极。六十年代初他还自我推荐编辑《刘少奇文选》,可是到了“文革”,他竟蓄意歪曲事实给刘少奇捏造大叛徒的罪名。但是要看到,康生的阴谋手段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没有那个历史时期的整个氛围环境,他是不可能如此得势的;而造成那种氛围环境的根源,恰恰应该追溯到从五十年代后期就不断升温的个人崇拜。 事实上,建国后张闻天是很早就提醒党中央警惕个人崇拜的,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苏共报刊上开始提出反对党的宣传工作中的个人崇拜问题,立即引起当时任驻苏大使的张闻天的高度重视,认为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件大事,并指示使馆工作人员收集整理这方面材料报送中央。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对此也是肯定的,将其逐篇刊载在中宣部的《宣教动态》上,毛泽东1954年在使馆报送的一份题为《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材料上批示:“此件,及去年冬季中宣部所辑关于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教条主义的一个文件,都是重要文件,宜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在京及在各地的中委、候补中委。”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明确肯定了苏共二十大在这个问题上的历史功绩。 可是,后来人们在批评苏共全面否定斯大林错误的同时,却将它这方面的积极成果也给抛弃了。就在1958年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个人崇拜有两种,正确的和不正确的,说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于是就有人在会上紧跟说:“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而正是凭阴谋家的政治嗅觉,康生早就敏感到这个风势的转向。1957年春他在向中央政治研究室干部介绍1956年《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时,报告的头一条就说:“《一论》和《再论》是基本相同的,但是有一点不同,《一论》中有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再论》中就不再提这个问题了。”于是接着他就认准这个风向大肆鼓吹个人崇拜,1958年他在一篇报告中抛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的“顶峰论”;1960年他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后标准”的“标准论”。 无论是“顶峰论”还是“标准论”,张闻天均有针锋相对的批判。对于前者,张闻天指出:“对于古人、今人和自己所发现的真理,决不应该认为是绝对正确和永远正确的”,否则,就是“绝对的、片面的、静止的、形而上学的、反科学的”;对于后者,他明确指出:“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尺度。”自然,张闻天的这些金石之言,在那种个人崇拜狂热年代,人们是根本听不到的。 对照之下,康生之所以得势,无非是他能假借个人崇拜,充分施展他那套既善于察言观色,进行歪理论证,又长于煽风点火,不惜制造伪证的特殊本领。而他这套本领那时之所以能运用得那样得手,反过来又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个人崇拜给什么样的人创造了生存发展的土壤和条件。邓小平说:“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主义统治的国家,因而封建主义传统的影响也特别长远。总之,在党的建设方面,特别是在如何考察干部选拔干部问题上,从康生此人的发迹史中,我们可以获得不少有益的历史教训。(转自《南方周末》) |
|||
|
|
||||
主编信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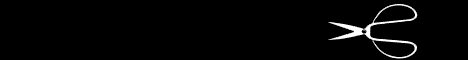 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中新社观点。 刊用本网站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