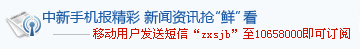荣念曾:我的每一部戏都是上一部戏的评论

我的每一部戏都是上一部戏的评论
他被称为“香港文化教父”,有着一批现已颇有名气的“学生”。 林奕华是其中之一,上世纪80年代初,初出茅庐的林奕华不时游说荣念曾帮他们排戏,后来荣应了他的邀请,加入“进念·二十面体”,林奕华便无比兴奋地成了荣的“小跟班”。梁文道也受其影响,在荣念曾的引导下走上了写政治评论的道路,梁文道称,“我们这一代的香港年轻人都受到荣念曾先生的极大影响”。
10月16-18日,“进念·二十面体—荣念曾实验剧场:夜奔”在上戏剧院上演。一个月前,在香港文化周新闻发布会现场,这个被太多人回顾并尊敬的“教父”级人物坐在记者的面前。他递上自己的名片,上面印着一连串头衔:香港当代文化中心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顾问、“进念·二十面体”艺术总监、香港艺术发展局创始成员名片太小,还有很多头衔印不上去。
然后,这个在香港文化界举足轻重的“教父”,从一个布袋子里拿出“进念·二十面体”的宣传册给我们,笑着说,“无论再多头衔,‘进念·二十面体’艺术总监的身份对我来说仍是最重要的。”
1982年,林奕华等人创办“进念·二十面体”,成员是一帮20来岁的年轻人,对剧场一腔热情,却苦于没有资金。开始是自掏腰包每人5块、10块,凑钱找地方排戏,后来决定收一元的“会员费”,由此吸引来了不少“会员”。他们采取集体创作、集体负责的管理,宛若一个艺术公社。那时候荣念曾比他们都大,在林奕华三顾茅庐般地游说下,于1985年正式加入进念当艺术总监,作为一个长者带着这帮年轻人做剧场实验。后来的很多香港文化名流都与“进念”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像黄耀明、刘以达、迈克、欧阳应霁、周耀辉等等,它就像一块吸金石,自己也闪闪发光。
在荣念曾的带领下,“进念”成了香港前卫戏剧的代表,在上世纪80年代对香港先锋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虽然林奕华在1989年离开“进念”去了伦敦,人员在不断地变动,但荣念曾一直留守岗位,对于“进念”来说,他就像是心脏,心脏在,生命力便在。
不断提问的老顽童
荣念曾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模样,说要给他拍照,马上做出各种搞怪的表情,像个顽童,只有两鬓的白发透露出他的年龄。
在采访中,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我喜欢向你们年轻人不耻下问。每次彩排的时候,我都会给学生们、演员们做一些问卷调查,了解他们的想法,再融入我的下一部剧中。”
今年儿童节,荣念曾跑去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天天向上”概念漫画展,他带来的名为“天天”的卡通形象让人们认识到这位“香港文化教父”的童趣魅力。不同领域的作品,只要有创意他就愿意去看、去学习或者尝试。
对于漫画主角的名字“天天”,荣念曾说:“我50年代在香港念小学时开始画漫画,那个年代内地每个小学的大门口影壁上都大笔书写着‘天天向上’这句标语,我也是在70年代到内地才见识到。标语写得很大、撑满整面墙,对小朋友来说一定很有压力。”这个名为“天天”的卡通人物多少有点反讽教育现状的意味。
与荣念曾聊天,他有时会答非所问,并且思维很快,一不留神他就已谈到另一个问题上去了。问他“你想通过这种实验剧场的方式取得哪些突破”,他说了两句就开始说教育,从戏曲教育聊到普通教育。后面的谈话中,他也不时地对教育唠叨几句,言语中透露着对“死背书”的深恶痛绝。
令荣念曾痛恨的还有“文化消费主义”,他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只成为一种文化消费的东西,他在剧中常常提问,是问自己,也是问观众,都是一些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关于剧场本身、关于我们的文化、关于我们的身份确认等等,他希望以此带来思考和交流,而不只是演一出戏让观众消费。
提问是荣念曾的习惯。他想与此次《夜奔》的合作者柯军的徒弟交流,问了对方108个问题;采访中,他会常常停顿下来反问你,或者不自觉地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他说一句“当然这也无伤大雅”,马上就开始一连串的发问“不过,大雅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思考”、“大雅是谁定的”、“雅的含义会不会改变呢”
这不断发问的习惯源于他对外界批判的态度。他早期还在报纸上写过评论批评自己的戏剧作品,别人不骂就自己骂。他真的希望有人来骂他的作品,当然不是谩骂,而是有建议的骂,这样能让他得到提高。
他说自己下一部作品是对上一部作品的评论。做了一个作品就不断地对它反思、提问,所以提问是他创作的源泉,可以说很多的灵感和创意是从他喋喋不休的提问中产生的。
我是荣念曾,我不是荣念曾
荣念曾有一个“香港当代文化中心主席”的头衔。这个中心是他1996年创办的,着力推动香港与各地的文化交流及艺术教育。2000年之后,他开始带领“进念·二十面体”着重进行跨文化跨地区的合作计划。如今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团国际顾问、香港-台北-深圳-上海地市文化交流会议主席。
文化交流是他1996年以来一直在推动的一件事情。荣念曾1943年生于上海,5岁时随父母移居香港,后来又到美国念书,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也习惯行走于不同文化之间。
同时他性格中有些“躁动不安”的情绪,从来就不喜欢守在一个单独行业、单一文化里。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荣念曾学的是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回港后,他却没有成为建筑师,因为不想把自己定在一个职业上。即使做剧场创作,他也在追求不断地“跨界”,或许是出于他永远不灭的好奇心,不断地研究京剧、昆曲,并与戏曲家合作创作出《实验中国传统三部曲》。
说到与昆曲家的合作,实际是一个巧合。当时荣念曾对昆曲的了解还停留在“一桌两椅”的阶段。在偶然的一次聊天中,音乐家瞿小松告诉他有个叫石小梅的人,在昆曲方面非常厉害,强烈的好奇心让荣念曾想马上去拜访此人。于是他们去了江苏省昆剧院,刚踏进兰苑剧场时,却看到柯军和孔爱萍正在排练,顿时被他们的精湛表演吸引,于是就有了后来与省昆、与柯军的合作。“柯军是个很有趣的人,”荣念曾回忆起两人最初的合作,笑声不断,“我曾邀请他去印度演出,在喜马拉雅山脚下他表演了《夜奔》,他说是给群山表演。”
如今荣念曾与柯军已合作了十几年,两人颇有默契。这次在香港文化周上演的实验剧《夜奔》便是两人合作的作品,柯军作为《夜奔》的主角有着极为精彩的演绎。
《夜奔》是明中叶戏剧大家李开先名作《宝剑记》仅存的两折戏之一,讲述了林冲被逼上梁山,趁着月黑星稀只身赶路的故事。在实验剧《夜奔》中,荣念曾借题发挥,论述表演艺术如何在政治动荡中不断发挥它的生命韧力。
这是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作为一个传统戏曲的实验剧场,《夜奔》不会只去讲一个古人的故事,渗透在整个演出中的,还有两代昆曲演员自身的抉择,是离开还是留下的抉择。同时,这是一个关于身份认同的故事,演员在《夜奔》中与林冲的身影交错起来,出场时喃喃自语着自我质疑的台词:我是林冲,我不是林冲多么熟悉的荣念曾式对白!私下里的荣念曾一定也曾喃喃自语“我是荣念曾,我不是荣念曾”吧。
没有研究的心态,就会自溺在感觉上面
B=《外滩画报》
R=荣念曾
借一个历史人物来关心当下的问题
B:在《夜奔》中,你一人担任导演、文本、舞台设计三职,哪一项对自己的挑战最大?
R:其实这些标签外在的都是别人加上去的,对我来说都是需要负真实责任的,因为这个作品是我创作出来的,每一部分都有参与。如果真的要说挑战性最大的,还是舞台设计,因为我喜欢低限,就是用最少的资源做到最好的效果。
B:《夜奔》的舞台背景看起来非常简单。
R:对,我是喜欢这种效果,也是我常常给自己的挑战。
B:做实验传统昆曲《夜奔》的想法是怎样产生的?
R:2003年的时候,是挪威与中国建交50周年,我接到一个去挪威的邀请,去做一个创作。我一定要找一个国内的艺术家跟我合作,所以就跟柯军说我们要不要一起做一个作品。那时我们正在讨论体制改革,《夜奔》更深层次讲的就是一个体制的问题。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戏曲来改编。包括传统戏曲也有传统戏曲的体制,这个体制现在需要去处理很多问题,要怎么去处理是需要我们讨论的问题。
B:《夜奔》里演员反复说的那句“我是林冲,我不是林冲”,是想表达什么呢?
R:那是关于自我认同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种林冲的感觉,很有可能会突然厌倦了现在所在的行业,就会选择离开原来的体制。每个人在某个阶段都会问自己,我对现在所在的行业如果不满意,我离开,要怎么离开,离开了之后要做什么。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其实是借了一个历史人物来关心我们当下的问题。
B:你想通过这种实验剧场的方式取得怎样的突破?
R:我不断在学,去了解传统戏曲里面的很多元素。我想我至少不会很表面地去看待传统戏曲。我不断想了解戏剧舞台是怎样来的,程式是怎样来的我更想了解柯军是怎么来的,他10岁开始学戏,那时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看待老师对他的教育,18岁之后他又怎么看自己,今天他又怎么看自己我很想通过这些演员来了解传统戏曲的教育与传统戏曲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也问柯军,传统的教育是背书,所以你是不是也一直在学背书?其实我们现在的教育都是这样的嘛,不光是戏曲教育,普通的教育都是这样,这里面有一些东西值得我们去讨论。
B:在你改编的《夜奔》里,有体现这个关于传统戏曲教育的问题吗?
R:有啊。其实我私下里和柯军的学生谈,我问他很多问题,问他戏台是怎么来的,昆曲艺术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他都说不知道,很奇怪。当然我又觉得他可能知道,只是选择说不知道。现在“我不知道”成了年轻人的口头禅,因为讲了之后可以不负责任,怕讲了我知道什么的话,就有更多的问题要讨论了。
B:创作《夜奔》本身也是你在不断摸索的过程。
R:对,我觉得创作本身就是在摸索,没有摸索就没有创作。摸索是很重要的,是需要很用心地去试的。我们有试着去搞一些自己不是很清楚的东西,都清楚了也不需要做了。
B:就是说,你在摸索自己的作品的同时,对它的演出效果本身没有很清楚的预设?
R:我觉得我们也不能一直去预计市场,像预计将来股票涨多少一样,没什么意思。但我们也在学着去关注,因为做一个演出,不仅是我跟柯军的互动、批评,也是我们跟观众的一个互动、对话。我们也希望一个演出能启发大家的讨论,而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消费,那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不断吸收实验的养料
B:你曾说演出完之后,写戏剧评论的人很少,感到遗憾。
R:我觉得有些可惜,越来越少有学者去认真地看、去分析戏曲创作。报纸上很多评论是给普通消费者看的。很多学者都是在兜来兜去钻字眼。真正要写一个评论的话,是要坐下来讨论、真的去了解。但现在什么都是追求快,没有人真的坐下来,慢慢聊,分析清楚这是什么,告诉你这个地方可不可以换一种方式做。要是这样的话这个评论家对我是有触动、启发的。但现在评论家只会说这个很好看啊、很时髦啊,就停留在这个阶段,根本没有一个更深入的对话。
B:听说你自己写了一些评论。
R:早期写过,我觉得很好玩。
B:对于《夜奔》这个戏你写过评论吗?
R:还没有。我越来越觉得我每一部戏都是上一部戏的评论。所以《夜奔》也就是我上一部戏《录鬼簿》的评论,《录鬼簿》又是对《荒山泪》的评论。就像你现在做一个访问的话,你应该超越你上一个访问嘛,如果你只是在重复自己的样板的话,那你就没有进步了。
B:你的创作哲学就是不断地超越自己。
R:不超越的话,就沦入一个商业轮回了。
B:矛盾在于,大家很多时候喜欢的总是有一个模式,好像美国大片一样。
R:但是你要看美国大片的导演,他们平常是在看哪些片子来得到灵感、来做创作的。百老汇的戏成功,是因为外百老汇启发他们去创作,外百老汇是从东城得到灵感,东城都是做一些实验性的片子。所以很多百老汇的人也会去看这种实验性的戏,他们是在不断吸收这些实验的养料。
B:你自已也会去看一些你的后辈做的东西吗?
R:最近比较少。有时候我会很感兴趣一些新的创作,不仅仅是戏的创作。你写的文章也是创作,如果你写得很有创意的话,我也会去看。其实舞台可以不仅是那种舞台,舞台可以很大、可以多样化。
B:你对舞台实验的热爱,跟你以前学建筑设计、学理科的思维有关吗?
R:学建筑给我最重要的启发是,房子是要基础的,没有基础是建不起来的,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需要基础。
B:做剧场的基础是什么呢?
R:对剧场本身的起步要很清楚。我去一个剧场就要了解这个剧场本身的历史、结构、长处、短处、局限,全了解之后,它会给你足够的力量去互动、合作。比如我跟柯军合作的时候,我希望了解柯军是怎么发展到今天的。这样我才真的可以跟他有沟通。
民间有很多力量非常有创意
B:你对昆曲的了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R:我开始是对“一桌两椅”感兴趣,这个跟建筑也有关系,舞台装置里面最简单的就是“一桌两椅”,我在这个里面去追求它的变化,在这种简约主义里再去寻求过一些抽象的演绎。之后我跟瞿小松有一次对话,他告诉我说有一个昆曲演员非常厉害,叫石小梅。我就马上说那我们去找她嘛,那时候我们在上海,他打电话给石小梅说我们要去拜访她。然后我们俩就坐火车到南京,跟石小梅见面,我在那次就见到了柯军。
B:这次见面影响到以后你跟柯军在昆曲上的长期合作?
R:对,后来我们就一直在一起合作。其实对我和柯军来讲,非常重要的一次经历是我们去印度。印度那边请我去做文化交流,我就问柯军,你要不要去一个跟你的文化背景完全不搭界的地方,一起做个交流。后来那次交流对我和柯军都很有启发,因为人通常都是通过看别人来看自己,每个人都是你的镜子。那次之后他们非常喜欢柯军,就邀请他再去,十几天不停地演出,每一场都有几千人。
B:他们懂昆曲吗?
R:他们很多人从来没有看过中国的昆曲。去印度的经历对柯军的冲击蛮大的,面对这么多人,他们不知道你是谁,你在干嘛。当然他们有好奇心,但如果这个好奇心只是一种对异国情调的好奇的话,这就要看我们怎么处理。
B:后来当地观众有对柯军的表演作评价以及后期的讨论吗?
R:当地的报纸有一些评价,评价挺好的。那次以后我们一直在讨论什么叫做文化交流,是作为一个文化大使去解说中国传统戏曲呢,还是解说中国文化,或者是去解说中国?这是不同层次的嘛。我们经常在交流,但这个交流是表面的还是更深层次的?是会推动经济利益,还是文化发展呢?要知道只有真正的交流才会有启发性,才会激发创意。我问柯军的学生108个问题,都是因为我很想跟他交流、沟通,了解他更深层次的一些想法。
B:通过《夜奔》,你最想跟观众交流什么呢?
R:这个要看观众啦。我在香港演戏,很多领导都会来看。当然他要表现他是支持文化嘛,这是表面的层次。另外一个层次是他真的想知道我在讲什么,有什么话我在对着他讲。
B:那你希望有一个怎样的平台来建立文化的交流、激发文化的创造呢?
R:其实我排这个戏的时候,已经知道会到世博会来,我就一直在想,世博会这样一个平台可以怎么样更好,就是说能不能让上海的文化更多元、有更多创意,因为上海的文化也是一个由上而下的文化,我其实觉得上海民间有很多力量非常有创意。
只有通过交流我们才有这个空间去评论,我可以去批评上海、南京,你可能在自己的体制里面有很多利益关系,不方便去批评。我觉得在文化交流的空间里是可以有批评的空间的。说明你关心、你有建议才会去批评嘛,如果只是很犬儒地说算了算了,那也就不会去批评了。
B:《夜奔》里也蕴含了很多对文化交流的反思?
R:其实我在《夜奔》里面有问很多关于我们自己文化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有一点自大,或者有一点自卑,我们是不是想得不够,是不是做得太少、计算得太多,等等,是不是这些全跟不自信有关系。我问了大概30多个问题,这些问题我跟合作的演员一起讨论,柯军跟我从第一条一直讨论到最后一条,年轻的演员只有头几条可以讨论,深了他们讨论不了。
林奕华的作品越来越单一化了
B:你现在有没有构想下一部戏怎么去“评论”这部《夜奔》?
R:我的下一部戏是这样的: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明年是十周年了,现在我们要怎样去回应它?我一直在跟柯军讨论,这十年昆曲发生了什么,整个体制、社会又发生了什么。我们也找了日本的能剧,日本能剧也是2001年被宣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我们应该做一个中国与日本的比较,在十年里面在创作上有没有什么拓展。
B:你不仅仅是在创作,其实也在做着类似学术方面的研究。
R:我觉得没有一个研究的心态的话,就没有创作的基础,会很自溺在感觉上面。在研究的过程里,我想知道得更多一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能够得到启发。
B:你怎么看待你的学生,像林奕华他们现在所达到的一些成就?
R:我一直跟林奕华说,你这样吧,退后几步跟国内的年轻导演去合作,不要再重复自己了。因为他的作品越来越单一化,当然这个是跟市场有关系,他在跟着市场走嘛,市场有需求,他就将它引进去了。
当然他还是做得蛮好。他每次演完戏之后请演员出来,每个人都在讲话、讨论。他将自己所谓导演的架子放下来了,在台上的时候演员在批评他,他也在笑。有这样一个平台,我觉得是他所有戏里面最重要的部分,每次完场的时候,这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我比较喜欢他那个《包法利夫人们》,因为他在里面将中产阶级很多问题提出来了,里面其实也在讨论文化消费的问题。他第一次演出是在台北的诚品书店里面,现在诚品书店越来越文化消费化了,没有再成为一个文化中心,越来越成为一个文化消费的中心。所以这个作品放在里面是有特别意义的,但好像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没深入下去。到大陆来演的时候好像已经失去了这个意义,有点可惜。
文/刘旭阳,陈虹霖 图/刘旭阳
 参与互动(0) 参与互动(0) |
【编辑:张中江】 |
Copyright ©1999-2024 chinanews.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