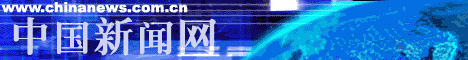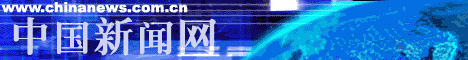中新网4月15日电 南方都市报报道,4月10日,武汉同济医院对外宣布,已按照卫生部脑死亡起草小组的最新标准,宣布患者毛金生死亡。据悉,这是我国正式认定的首例脑死亡。同时,同济医院在该患者逝世一个多月后,公布了他在医院抢救和接受“脑死亡”诊断全过程的录像资料。
2月23日,患者毛金生因脑干出血送进同济医院。虽经多方救治,仍深度昏迷,无自主呼吸,不过心跳还维持。征得家属同意,医院严格按照国际通行的脑死亡标准和我国卫生部《脑死亡判定标准(第三稿)》,对他进行了3次脑死亡诊断,结果均为死亡。
毛先生的亲属和子女,在了解了脑死亡的真正涵义后,郑重在放弃治疗协议书上签字。2月25日23时05分,帮助毛先生维持了30多个小时呼吸的呼吸机被拆除。21分钟后他的心脏也停止了跳动。
作为我国严格按照卫生部颁布的《脑死亡判定标准(第三稿)》诊断的第一人,毛金生的诊断过程及整个录像资料,为我国脑死亡观念的更新和立法的推动,将起到巨大的作用。
人物档案
张苏明
1952年生,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常务委员。
1991年至1994年,留学美国明尼苏达医学院神经病学专业,长年从事脑血管病研究,是我国推进“脑死亡”立法的重要人物。
4月10日,武汉同济医院对外公布了我国第一例“脑死亡”病例的完整录像资料后,张苏明教授每天接到的记者电话不计其数,用他自己的话说“感到害怕了”。但是,作为积极推动我国“脑死亡”立法的重要人物,他与他的同事们在作出全国首例“脑死亡”判定时,并没有感到胆怯。他说,这件事之所以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是因为它挑战了我们几千来固守的“心死亡”的死亡判断标准,挑战了中国人的传统伦理观念。
前日,记者在武汉采访了张苏明教授,第一次感受到了两种死亡观的正面交锋。
推迟了一个多月公布
我们把这件事当成科学事业做,而不是把它当成新闻事件
记者(以下简称“记”):实际上毛金生老先生早在2月25日就被诊断为“脑死亡”,并放弃了治疗,但直到4月10日,同济医院才对外公布这件事,推迟了一个多月,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张苏明(以下简称“张”):首先我们要做好认定工作,资料需要汇总,因为我们是在把这件事当成科学事业做,而从开始就不是把它当成新闻事件;再就是病人家属一时还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他们的亲人刚刚过世,悲痛万分,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宣布,是有悖常理的,我们要尊重家属的意见,做好家属的安抚工作,再有就是,在我们医院做全程性记录的同时,当时参与监视全过程的记录者之一的中央电视台,他们制作节目需要时间。只有各方面的条件都成熟了,我们才能对外公布。
第一个“吃螃蟹”
认定脑死亡势在必行。盖子总是要揭开的,早揭开总比晚揭开好
记:在毛先生之前,上海、南京也出现过脑死亡的案例,为什么只有武汉同济医院敢于作出称之为“全国第一例”的脑死亡诊断,同济医院为什么敢于吃这个螃蟹?
张:敢这样做,首先是因为医院领导的重视,认定脑死亡势在必行,应该推动立法的进程,如果长期拖下去,可能就长期得不到法律的认同,得不到社会的重视。在一年多之前,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关于脑死亡问题的协作工作组,由我们医院各重要科室的医生组成,这次的第一例案例就是在这个协作工作组的领导下执行的。
记:在我国,脑死亡还没有立法,应该说同济医院的这次诊断是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条件下进行的,您认为这是在冒险吗?
张:我不认为这是在冒险,即便这需要承担一定风险,但这种承担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国家的科学界、医务界其实长期以来都认识到脑死亡的意义,但好象谁都不愿意去挑这个头,但这个事情总是要有人去做的,盖子总是要揭开的,早揭开总比晚揭开好。
多做了一次脑死亡测试
第三次是当着死者众多亲人的面做的,希望他们能理解“脑死亡”的概念
记:按照国际惯例,一般脑死亡的测试只需两次,但这次你们做了3次,这是为什么?
张:我们按照医学上的临床判定检测标准做了两次,第三次则是当着毛先生众多亲人的面做的,希望他们实际看到,能接受这个死亡的事实,理解“脑死亡”的概念。
记:现在毛先生的家人遇到了来自社会比较大的压力,对这件事,您如何评价?
张: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我相信占主流的舆论是支持医学向前发展的,有个别不好听的非议可能还是基于传统观念,旧观点。
记:当时对毛先生的3次测试,您都在现场。当第3次测试结束的时候,您对确诊他为脑死亡,心里有底吗?
张:实际上做第一次的时候,我就有底了,但还需要核实,需要更多专家的认定,并不是我一个人、我们一个科室说了算的。
家属的理性反应很了不起
亲属们能够同意放弃无效的治疗,接受科学的事实,我觉得很了不起
记:当3次测试结束,判定毛先生脑死亡的时候,他的亲属反应如何?
张:我们把情况向他们作了说明,他们作出了非常有理性的反应,他们说“我们不懂科学,但我们尊重科学”,同意拔管,同意放弃无效的治疗。我觉得当时的场面是很感人的。
记:在拔管之后21分钟,病人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您是什么样的心理?
张:我觉得出乎意料,我们群众有这样的觉悟,能够认识科学,接受科学的事实,我觉得很了不起,我觉得最值得赞扬的是我们的家属。
记:对家属的反应,作为一个医学工作者,您感到欣慰。
张:是的,死亡是一个自然过程,本来很多病人都应该这样,但是很多病人都不能这样,我们只有勉为其难地在那里进行无效的治疗。从此以后,可能开了一个比较好的先河。
以立法严谨保障操作规范
必须有一定的资格认证,如果说乡镇卫生院也来搞一个,那就乱套了
记:传统的心脏停跳、呼吸停止等确定死亡的依据,都是按照公认的医学界的标准进行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常识,那么,为什么您特别强调脑死亡的标准要立法加以确认呢?
张:在没有立法之前,不排除有人滥用权力的可能,所以,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关键就是为了促成立法。立法的必要性是在操作层面上的,通过一种法律程序,通过科学的认证,一个群体而不是单个人的认证,主要是防止因为脑死亡而出现其他更复杂的情况,特别是犯罪。如果将来立法了,判定脑死亡就可能只是一个常规动作,但这个常规动作要有一个规范化的操作程序,不能够随心所欲地判定病人脑死亡。
记:您认为脑死亡的立法应包括哪些方面?
张:当然这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法学家们可能会比我们考虑得更严谨一些。就医学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应该按照诊断标准来操作,必须由专科大夫来确诊、认定,而且还不止一个专科大夫。我说的专科大夫是神经内科的专家、神经外科的专家,甚至麻醉科的专家、急诊科的专家,我想应该成立一个工作组吧,这样操作比较稳妥一些。
记:每个医院都要有吗?
张:必须是有一定规模的医院,必须有一定的资格认证,不能随心所欲,如果说乡镇卫生院也来搞一个,那就乱套了。
记:现在,脑死亡立法面临着怎样的困难呢?
张:主要是老百姓在认识上还有传统观念的束缚,再一个就是,脑死亡能不能为广大的立法工作者认同,我相信也有一个过程。站在医学的立场上,支持我们的人可能会多一些;但是站在法学、社会学的立场上,则要考虑的问题可能更复杂一些。立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法规、一个大家愿意共同遵守的公约,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脑死亡的隐蔽性和公开性
不能简单地说把所有的权力都交给了医生。我觉得将来家属都是可以参与判定的
记:现在,有法律专家认为,脑死亡有相对隐蔽性,只有专业医生才能判定,如果脑死亡立法,意味着把死亡的判定权交给了某些医生,这样,医生手中有了特权,会不会导致某种条件下的滥用或者非法使用?
张:有这种可能性,所以立法的条款应更加仔细。不排除有个别极端情况的发生,但也不能简单地说把所有的权力都交给了医生。因为,判定脑死亡有共同的指标,神经系统的检查是有特征的,比如说,心电图,它不蹦了,你还能说他心脏还在跳吗?脑电图,完全是平直的,你还能说他有脑电波吗?如果TCD完全是个振荡血流,你还能说他的脑子里有血流吗?所以说,它虽然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但还有一些在精密科学仪器上都显露出来的公开性指标,我觉得家属将来都是可以参与判定的,比如我刚才说的那些,都是非常生动、形象化的特征性图形,任何人都能明显地看得出它们与正常图形的差异。
记:那么,如果想要避免今后发生在脑死亡方面的医患纠纷,您认为立法应注意什么?
张:要更加严谨。通过我们的实践可以暴露出问题,通过暴露出来的问题,立法可以做得更严谨,我想,把法律的漏洞弥补到最小,使利用法律漏洞钻空子的机会达到最小,这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当然,可能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
记:有报道说,脑死亡可能在今年就得以立法,如果真的是这样,您会不会觉得有点太快了?
张:能不能立法取决于立法机构的认同程度。当然,我相信通过我们这个事情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立法的进程,但是到底有多快,我还不敢说。
“脑死亡”“心死亡”可能并行
病人家属的意愿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认识脑死亡,还需假以时日
记:从您的话里,我感觉在涉及脑死亡的判定时,您特别关注病人家属的感受。那么,以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您认为是否必须把对病人家属的尊重放在第一位呢?
张:我认为是这样的。病人家属的心理状态、精神状态应该得到充分理解,他们的意愿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如果病人已经脑死亡,而家属想以心脏停跳来认定死亡的话,也是可以的,医生不会强迫病人家属一定要接受脑死亡的死亡标准的,但医生有责任将脑死亡的现状告诉病人家属。
记:也就是说,以后可能实行“心死亡”和“脑死亡”两种方式并行?
张:有可能。毕竟让大多数人接受脑死亡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记:关于脑死亡的意义,有人认为,医学界显得太功利了,为了节约医疗成本就不顾几千年形成的伦理道德。
张:我觉得这种评论是不公正的。资源的浪费其实是双方的。脑死亡的病人长期占据病床、浪费大量的医疗资源,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这对医疗单位都是一种浪费,同时更重要的是,对家属也是一种浪费啊。
记:我想请您进行一下角色置换,如果您不是脑死亡的研究专家,不是一个神经科医生,当您的家属碰到类似的情况时,您是否能接受脑死亡的概念?
张:假若我的亲属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医院能够拿出十足的证据,说他脑死亡的话,我能接受这个事实,这是科学的态度,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记:如果请您对毛金生老先生的家人说一句话,您会说什么?
张:我非常敬重他们一家人,他们是一个高素质、非常和睦的家庭,不能说文化程度都很高,但确实是非常善良、理性的一家人。我能理解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也敬佩他们对医学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记:如果请您对不能理解毛先生亲属的街坊邻居说一句话,您会说什么?
张:对说闲言碎语的人,无须过多地指责,认识脑死亡需假以时日,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观点强加给任何人,但我相信公众会逐步理解并接受“脑死亡”的。(王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