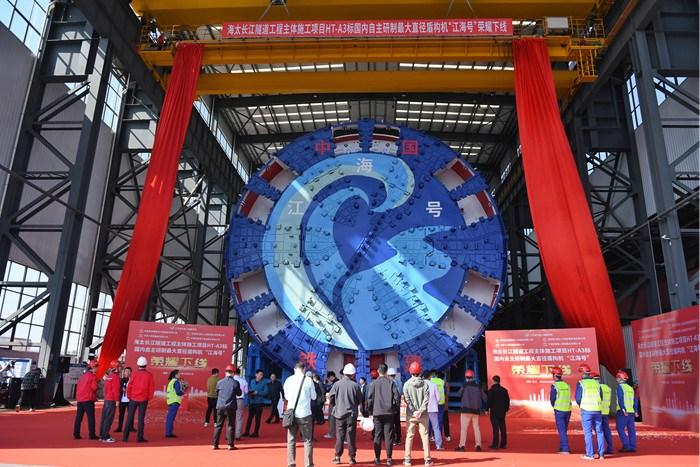黄永玉:我仅仅是个有点头脑的弱者
 参与互动
参与互动98岁出版诗集《见笑集》 接受专访
黄永玉:我仅仅是个有点头脑的弱者
98岁黄永玉先生的全新诗集《见笑集》由作家出版社在年前推出,书中收录黄永玉1947至2021年间创作的150余首诗作。从1947年的《风车和我的瞌睡》,一直到2021年的新诗《春》,将他饱藏着近一个世纪生命体验的情感完整呈现在读者面前。黄永玉为此诗集亲自绘制封面内外图、题写书名,挑选并朗读部分诗篇。
和黄先生聊天久了,会发现他常落脚的一句——“真是了不起”,加上他特有的满透着真诚的着重语气——那通常是在夸奖旁人。
年轻朋友节前送了他一颗球状植物,不需任何营养和水便能接连开出五六朵红艳艳的花,他连连感叹大自然的神奇。
纵然早已名满天下,他依然对周遭这个并不完美甚至颇多驳杂的世界保有着满满的亲近和热忱。13岁出来“混”江湖,如果没有两把刷子,很难在遍地狼烟里立足,那一路艰难跋涉,免不了要与各色人等周旋,人情世故不说练达,也要精通不少。可在和他聊天时,丝毫不需要有任何防备,你完全可以相信他口中的往事故人。这是一个纯真得让人既敬且爱的人。
身处困境,明箭暗箭纷至,遍体鳞伤亦不降志辱身。大抵人在困境或绝境中,也只有诗歌这种凝练蕴藉的形式才更能明志吧。几十年后的去岁夏天,黄先生从旧纸堆里重新发现了这些诗稿,兴奋地戴着墨镜坐在院子的阳光里边抄边读,俨然又回到了那个率性的诗歌少年。当然,身后已是百年苍茫。
黄先生的诗歌创作一直延续到当下,2021、2022年亦有新诗落稿。很多读者留言,说不期然在《非梦》前破防。那是诗人95岁时所作,至简的语言背后是至深的同情与悲悯。
采访黄先生,不少朋友留言说希望他可以谈谈长寿秘诀。大概是被问太多次了吧,黄先生索性在《“我想不到的长寿秘诀”》(收入散文集《不给他音乐听》)一文中做了回应,那是我听到过的最睿智的答案了。读完这篇,脑海中自然浮想起6岁的黄永玉在家乡白羊岭“古椿书屋”的木板墙上写下的两行字:“我们在家里,大家有事做。”这位湘西汉子践行了一辈子。他一直奔赴在自己的热爱里,一刀刀、一笔笔、一字字地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
高尔基在谈到契诃夫时说:“我认为每一个人,到了安东·巴甫洛维奇身边,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产生了一种愿望:希望自己变得更单纯,更真实,更像他自己。”黄先生也有这种磁场,走近他,会不自觉地有种想要变得纯粹、干净的希冀。那一日日坐在春风里的聆听,在多少年后,都会是最温暖的回响吧。
1
见笑见笑 旧时代的客气话
问:新书为什么取名《见笑集》?
黄永玉:我原先不知道,清朝有一个人出了本《见笑集》。这是我想了两天想出来的,见笑见笑,旧时代的客气话。假客气真客气混在一起的,说好说歹就是这么一回事。
问:您的书名都很特别,像《比我老的老头》《这些忧郁的碎屑》,您有何诀窍?
黄永玉:没有诀窍。不要太在乎,但反过来说,你要有一点取名字的基础,你要有点底,要读点书,还要在江湖上混一点。
问:这本诗集收录的作品从1947年一直到2021年,写诗时的心境和处境想必也迥异。“文革”期间您也有过“写了又怕,怕了又写;今天藏这里,明天藏那里”的时候,是什么支撑您坚持写下来?如今回看那时候写下的文字,有何感想?
黄永玉:这么要紧的东西,很容易忘记的,那就写下来留起来。要是给查到了当然要倒霉了。不过“文革”时抓我不是为我写东西这个事儿,是要问我认识什么人,跟他们说些什么话。朋友都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可靠。我的老小生熟的朋友都放心,因为我不会讲的。为什么我不会讲?我这一讲,朋友会吓得半死,你这时候吓他干吗,我不会讲的。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嘛。
我庆幸那段时间没有做这类的事。我整个“文革”就是靠说谎过日子的。靠说谎装病日子过得挺好,我一辈子说谎的修养全用上了。我装我有传染病的肝炎,没有人敢跟我一起生活,专门给我了一个小屋子。
问:读《见笑集》里的很多诗,诸如《被剥了皮的胜利者》《毕加索会怎么想?》《非梦》,很明显地感觉到,您更愿意站在弱者立场上。
黄永玉:我本身是个弱者,我哪能站在强者的角度?我仅仅是个有点头脑的弱者。
2
你是不是大师,你自己问自己
问:您是不是很不喜欢被称为“大师”?
黄永玉:你是不是大师,你自己问自己。什么叫作大师你要弄清楚,人家喜欢你,称你大师,你就真以为是的话,那大师有什么价值?你不知道你不是大师吗?你有什么资格?达·芬奇是大师,你算吗?不做大师你过不了日子了?
问:您不工作也不读书的时候会想什么?
黄永玉:这种情况很少。不读书不工作的时候想朋友来玩,来聊天。我有很多种类的朋友——有读书的朋友,有不读书的朋友,还有吹牛的朋友。
问:您最近在看什么书?
黄永玉:前几天在看美国的《大亨小传》。那一帮小说家写得最像文学。写两个人在一起——“他们两个人大概只隔了两尺距离的黄昏……”点出了周围的那些人的关系。我想这个比欧·亨利这些更文学一点。这两天看《雪国》,讲故事的多一点。都是老书。看了又看。
问:经历过这么多磨难之后,还能如此豁达,想请教您是如何做到“不执着”的?现在的人抑郁的越来越多,年轻人也活得越来越丧。
黄永玉:不要认真。不怕死。不要羞辱自己,要自重,要自尊,要把自己当人看,不要去讨好,不要去逢迎。
问:有没有想过,如果这辈子没有当画家和作家,您会做什么?
黄永玉:没想过。不会想这些。
问:您喜欢的东西很多,那您讨厌的东西呢?
黄永玉:我最讨厌的就是对人不诚实,对朋友不真诚。
3
你不要以为自己天下第一,真的不是这样的,要清楚
问:您在很多地方生活过,觉得哪里是家?
黄永玉:离开家乡后到过很多地方,后来去上海、台湾,再后来到香港同老婆生活在一起,比较稳定了,穷还是穷。1953年再一起回北京,有了家了,飘荡啊。回到北京,不光是有了个家,还有了这么重要的工作——在美术学院教版画。
刚回北京时感觉非常生疏,不熟悉。我什么都尊敬,什么都听话。
美术学院有很多派——有延安来的,有北京市的,还有华北大学,也就是当年的华大。我呢,就是一个人,哪派都不是。除了看书,就是到外面打猎,听音乐,在家里刻木刻。刻了很多,每年出很多作品。学生呢,有喜欢我的。因为我政治上没有本钱,喜欢我也不敢太亲近。
问:这不就是您在《假如我活到一百岁》那首诗里说的——我和我自己混的太久,我还是觉得做我自己好。
黄永玉:这句话不是我自己说的,《世说新语》里的——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
问:艺术这条路上孤独寂寞的时候多吗?
黄永玉:没有寂寞。艺术这个东西,有人欣赏,欣赏里面的东西复杂极了,有时碰到马屁客希望你送给他……复杂。这个场合你要保持冷静。实际上我觉得我这一辈子画的画没有什么的,并不好。为什么,好的太多了。画得好的人太多了。你不要以为自己天下第一,真的不是这样的,要清楚,你就规规矩矩老实地画了。求实的态度不是为了成第一才画画。办不到的,怎么办得到?
问:有没有觉得特别难或者绝望的时候?
黄永玉:还不至于这样。不存在这个绝望。我只能说我画完一张画总是表示遗憾,接下来画又有新的遗憾。现在那一张克服了这个问题,但是也有新的遗憾。人家以为黄永玉你讲假话,虚伪啊假谦虚啊,实际上就是这样。艺术的创作过程是一个遗憾的过程,永远在遗憾。人家艺术家遗不遗憾我不知道,大概伟大的艺术家不遗憾,像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毕加索,他们就不存在遗憾。
4
运气是给好心的人
问:凤凰对您的影响是不是贯穿一生的?
黄永玉:我讲一件事。捉迷藏蒙眼睛。凤凰小孩子经常玩,不蒙眼睛的,脑袋撞到柱子都肿了,闭着眼睛哭——我们这样是标准。我们到外面江湖以后做事,遇到什么事,我说“不怕”,这个是凤凰的特点。
问:您觉得自己是运气好的人吗?
黄永玉:运气好是鼓励一个好心的人。我心还好。就是这样。运气是给好心的人。我相信这一点。
问:您现在仍保持着充沛的创作力,想问问您的脑力和体力是如何保持的?
黄永玉:不要摔跤。摔跤就像我现在这样。脑力就很难说,可能和遗传有关。别害病,脑子别损坏。我的算术零分,物理化学都不行,数学谈不上,几何还不错。这个很难讲。我本人哪里懂得这么多的分析自己的东西,不可能。
问:成功有没有捷径?
黄永玉:我哪有什么捷径。有的文章写得好长好长,写完了看着显得不好,就不拿出来了。我现在没有拿出来的有的是。
问:《见笑集》里有一首谈到如何对待嫉妒——“怎么办,欣赏就是”。真的能做到吗?
黄永玉:不是做不做得到,是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告诉你,还是那五个字——爱、怜悯、感恩。重点是怜悯。我是弱者怜悯强者,对那个欺负你的,你怜悯他:“怎么这么蠢啊,你的时间都浪费在欺负别人,回去看看书画画画,认真的多好,这么蠢,你看我现在占便宜了吧。几十年一晃荡过去了,一本书也没有……”
问:您属于好奇心比较强的人吗?
黄永玉:好奇心我好像很少,还有冒险。我很少冒险。我干吗要冒险。还有打架也是,我干吗去打一个无聊的人,打架可能有生死的问题,我这么有价值的人怎么同你比,所以不打。不值得。
问:您属于聪明的人吗?
黄永玉:我认真。我是个认真的人。人家半分钟想出一个道理,我要好几天,人家不知道就是了。我在家里读书,人家不知道。
问:有没有过后悔的时候?
黄永玉:有有有,我还没有想我哪一点后悔。
问:那就是没有。
黄永玉:不,会有的。对不起人的,有的。
问:这世上是不是有些事就是永不饶恕,跟时间过去多久并没有关系?
黄永玉:巴黎圣母院左边不远处草地上,有一个很窄很窄的石阶,大概一米宽都不到,往下走,原来底下是一个小圆厅,是一个纪念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法西斯屠杀的几十万死者。阿拉贡代表性的句子在正顶上——“可以原谅,不能忘记!”对此我有不同意见——不可忘记,不可原谅。
惩罚是一回事,实际的报仇是一回事。尤其是我本身没有力量,你报什么仇?你惩罚谁呀。所以我一辈子说爱、怜悯、感恩。我怜悯欺负我的人,怜悯那些残暴无知的人。怜悯是因为我们不能反抗,所以怜悯。要是能反抗,我可以揍他个半死。像我的两个广东学生,星期天老到我家里玩,来吃饭,我对他们这么好,“文革”翻了脸了,到我家里抄家,把古代的东西看都不看乱敲乱打。我说:“你这两个小子,在以前,我拎着你们的裤子就把你们挂树上。”世界上这么多残暴无知的人在欺负人,你讲道理他听不懂,他没有文化,这很可怕。那怎么办呢,回家看书,工作。
5
变成骨灰
跟那些孤魂野鬼在一起
想到哪就到哪去
问:丁聪说您写诗、刻木刻、写剧本、画漫画、搞雕塑、写散文和杂文、画国画,又写长篇小说,什么都做,而且都做得很精,不知道您还有什么不能做的?
黄永玉:生孩子。数学我也不会。我还能的你现在没有看,当时看就好了——打架。解放前打架,每离开一个单位都是因为打架。(打架)有一点厉害。我学过。
问:您现在看着脾气很好。
黄永玉:哎呀,你不知道我老讲我现在这么细心,就是刻木刻培养出来的。刻木刻一刀一刀,在画里面一个小球里有很多细线,以前那个着急的脾气怎么受得了。我解放以后回到北京,没有打过架。当年离开《大公报》是因为打架。我要打架的那个人,后来也回来了,来找过我。三年困难时期,他在广西住,还准备过年杀猪送我一个腿。我以前打架很厉害的,现在连个水瓶子都开不开。
问:您曾经安慰过黄霑:“失恋算什么呀,你要懂得失恋后的诗意。”怎么讲?
黄永玉:黄霑这个人就是个调皮大王。他和林燕妮在一起,后来林燕妮不要他了。我们住在一条街上,在半山,比较安静,他有时来找我聊天,林燕妮也见过,见得不多。那时候我写黄霑,林燕妮在公开文章里说黄先生老写黄霑,为什么不写我。也是开玩笑。
大庭广众最好不要跟林燕妮在一起,她会出你意料地穿件你想象不到的衣服。我开画展,她来参观,一进门大家看着她——紫罗兰色的鞋,紫罗兰色的纱纱衣服,戒指、手套也全是紫罗兰,帽子斜歪着,你说害怕不害怕?但是人家是好心,你也不能怪人家。她真有文化,能写东西。家里还有钱。黄霑为什么和她分了,谁知道?他来找我,我告诉他,失恋你要欣赏失恋的诗意。
我在香港与不少演员朋友有来往,我不把他们当做明星。周润发来,我有时候在家,有时候不在家。不在家,工人不让他进。他说让我进去喝杯水看一看。不让。“我是周润发。”“我知道你是周润发。”
问:您有没有害怕过什么?
黄永玉:我想想看。有人晚上怕鬼,对我来讲,不存在这个问题。我做梦从来没有让鬼追,从来是我追鬼的。在我家乡,白天看到死尸,放到棺材里多少年,等很远的亲人来接他。结果接不了了,棺材困在那里,我们那里叫长亭还是短亭,旁边盖一些小屋子,我经常逛来逛去看一看,还有味儿,都惯了。真是,不怕死就不会怕鬼。死就一次,疼两秒多钟,一下就过去了。
问:“到了老年作诗,不再想当诗人了,只是像个账房先生,小心地作一些忧伤的记录!”虽然说是“忧伤的记录”,很多人还是读出了豁达。您怎么理解变老这件事?
黄永玉:这是五十岁的时候写的,距离现在快五十年了,但是感觉写的也没有错,而且马上就来了,一年两年三年就死了,有什么好怕的。我关照律师关照女儿黑妮,把我送到火葬场就回来,骨头就不要了。想我的时候怎么办,看看天看看云,用不着走到老远去。千万不要进八宝山,死了以后还要过规范生活,我受不了。痛苦了一辈子,死了之后还辛苦,不要。自由,变成骨灰,跟那些孤魂野鬼在一起,想到哪就到哪去。也不用坐飞机。还省地方。世界上哪里有你的朋友成天为你悲哀,有的时候想想你就好。
该怎么活就怎么活。我幸好没有喝酒。喝酒浪费了时间,身体也搞坏了。我这个身体不好是摔的,不是因为病。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喜欢买酒给朋友喝,一直到干校。国庆节端午节,“黄永玉,国庆节到了。”然后我就买酒,看着大家喝。
采写/姬小琴(《见笑集》责任编辑)
文化新闻精选:
- 2024年10月31日 16:46:30
- 2024年10月31日 13:21:30
- 2024年10月31日 12:40:11
- 2024年10月31日 12:03:31
- 2024年10月31日 11:29:23
- 2024年10月31日 09:45:28
- 2024年10月31日 00:25:03
- 2024年10月30日 16:55:02
- 2024年10月30日 16:39:33
- 2024年10月30日 16:3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