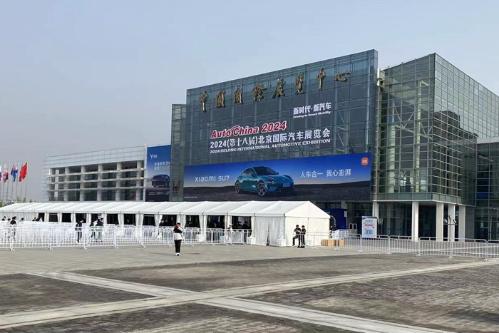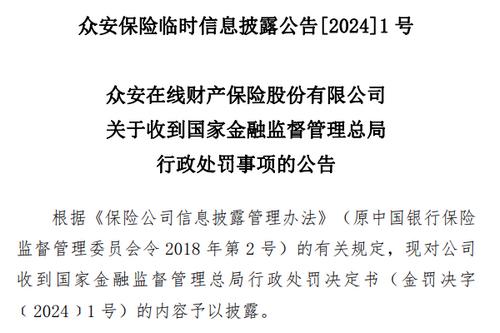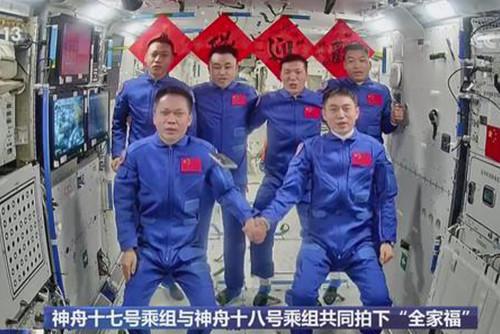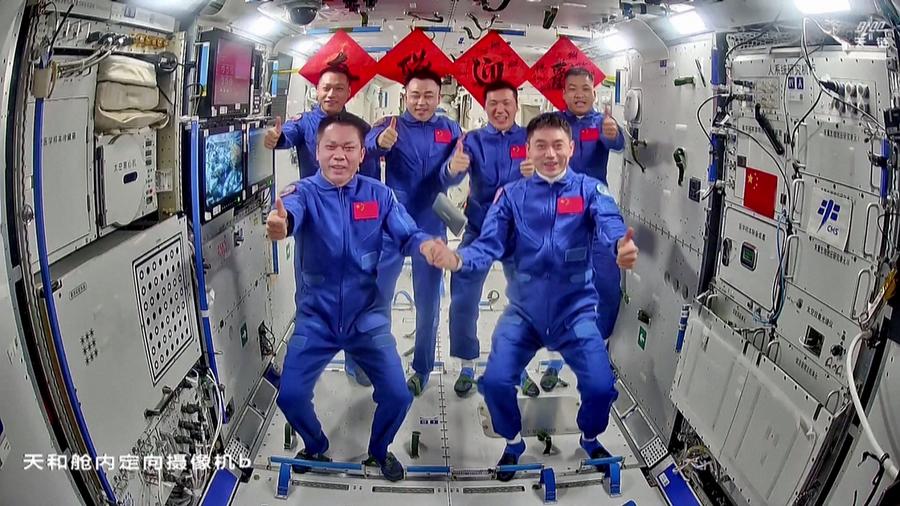专访路内 想创作另一种身份
 参与互动
参与互动专访路内 想创作另一种身份
在很长时间里,“路小路”就像是路内身上一个黏滞的标签,甩脱不掉。在很多读者眼里,路内就是路小路,而在另一些人眼里,路内只能写路小路,只能写自己经历的事。作家如何面对只会写自己这样的指控?作家如何调用新的写作经验,开创新的故事?
小说的任务不是阐释命运
新京报:《雾行者》虽然写了一群文青,但从职业或者从社会地位来说,他们还是相对比较底层的。你好像对书写这样一种偏底层的人物有持续的兴趣?
路内:《慈悲》和《花街往事》还算,但这个说法对《少年巴比伦》来说其实不恰当。在《少年巴比伦》所写的年代,中国并没有“底层社会”这一说,他们都是平民。《雾行者》确实如你所说,出现了底层,但仍然没有出现中产。1998年的时候,中国是没有中产阶级的,大家仍然是在底层中间翻涌。
比如,我作为东南沿海的平民,见到了内部省份来的平民,那些平民比我穷得多,他们到我的城市里迅速构筑成了底层。我啥事都没干,就变成中产阶级了。这感觉是很糟糕的。那些年轻人为谋生而来,当然不可能带上自己的家当,当然是因为比你更穷,才到你的家乡来谋生。几十万人来到这里,你就变成中产阶级,在那个年代可能你还挺有优越感的。但你一毛钱都没多挣到,这种感觉其实是非常虚幻的。
但经过时间它慢慢夯实,凝固起来了:就是有一个生活在城乡接合部的阶层。北京也有近郊,近郊掺杂本地人和外来人口,外来人口居多,这里面形成了底层,如果底层进入城市中心地带,会被查暂住证,在那个年代是会被遣送回去的。这个概念没有明确的形成时间,但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我要写的话,本能地会关注这个群体。
但我关注不到农村,我对农村的生活非常陌生。我去过农村,好的农村当然也有,但也有穷的。但我不会把他们当底层,那不叫底层,那就是农民。在城市会出现底层的概念,我们实际上是以城市标准在讲述整体的社会阶层的标准。
新京报:除了底层身份之外,他们另一个非常鲜明的身份是文学青年。
路内: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是文学青年,说实话这是有意为之。我当然也可以写一个单单是底层青年的小说。我的一些朋友说你这样写不合算,你应该写成两个长篇:一个关于文学青年的长篇和一个关于底层的长篇。但回过头来想想,如果单写成两个十几万字的长篇,多么单薄。它就是10年前的故事,无法讲述更多或者无法投射出更多的意义,而小说就是在不断地叠加中产生了2+2>4的意义,不是1+1>2的意义。
新京报:具体来说,文学青年为你的小说增添了怎样的意义?
路内:很有意思的是,他们讲述的就是“意义”这件事儿。这里面有极度自反的东西,自我反对。看这部小说,你会觉得这群人怎么前言不搭后语?前面讲的东西跟后面是矛盾的。他们讨论什么叫做深渊,最后又否定了深渊;讨论什么叫做虚无,最后说其实虚无也能讲出它的意义。是的,经过了十年,人就是这样。
他们的文学观怎么看上去那么彪?这种极端的东西,并不一定是文学观,这是他们的世界观,只是他们在用文学观掩盖世界观。面对一个高速变化的社会,他们没有很好的世界观能够面对,就拿文学中间的观念套用到高度变化的世界中去,就像一个赤裸的人,虽然没有衣服,拿一块麻布出来也能遮挡住身体。
但是,至少文学还是能教会人一些东西,什么是高尚、什么是卑鄙,大概有点认知。没有受过文学教育的人,对于高尚、卑鄙、羞耻感的认知会单薄一些;即使是很贫穷的那些人,受过文学教育也会更好一些。
我想与成名作家“路内”割裂
新京报:《雾行者》从1998年写到2008年,期间发生了大量影响很大的事件,包括洪灾、非典等等,但你其实并没有大篇幅地直接描写这些事件,只是让它们作为小说的背景,这是你有意为之的吗?
路内:不能说有意,也不能说无意。如果一部跨十年的小说写的是那些在中国南北跑来跑去的年轻人,似乎一定会提到这些事件。如果以电影的载体来表达的话,这些事件跑不掉。因为那十年,中国的媒体和信息已经进入一个很发达的年代,来自五湖四海的每个人都会带来自己家乡的见闻、消息,所以一定会讲到非典、洪水这些东西。
但是,我提到这些事件,显然也不只是为了安插这些元素。每一个不同的事件,似乎构成了小说空间里“十年”的一个个节点,好像这些事情恰好是他们生命旅程中间的一个拐弯点。这就像千禧年,千禧年是不存在的,是人为设计出来的。但是,人们仍然跟随着设定出来的那个时间点去欢呼,去倒计时,去自我认证。那些发生在远方或者说其他地方的事情,可能没有直接影响到主人公的生活,但它仍然间接地在改变着这些人的认知方式。
新京报:为什么会选择1998年到2008年这样一个时间段?
路内:那个时间段正好也是我自己特别年轻的时候,25岁到35岁。这是人最有驱动力的年龄,对于我自身来讲,也是最好玩的十年。整个中国社会挺松散的,气氛特别欢乐、向上。看GDP就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每一年都比上一年好,你想都不用想,都会知道明年一定比前一年更好,呈现这样一种趋势。
新京报:你参加匿名作家竞赛的时候,将《雾行者》的一部分改写成了短篇小说《巨猿》,怎么理解这种从长篇小说到短篇小说的改写?
路内:这挺有意思的,《巨猿》本身就是在长篇小说里转述的一个短篇小说,它不是《雾行者》的一个故事的片段和过程,它是《雾行者》里端木云读到的另一个虚构的人写的短篇小说。它是这个长篇里的一部分,但它同时也是突出的一部分,它像突出来的地方,所以可以被单独拿出来。
我们可以说《巨猿》像故事梗概,它是个转述的小说。我当然可以把这样的小说扩写成一个两三万字的中篇,但我没这么做。在匿名作家竞赛里,《巨猿》仍然是作为一个短篇小说中存在的另一个人写的书,似乎我从来没有写过《巨猿》的故事,而是另外一个虚构的作家写的。
它就像是我曾经读过的一本书,但这本书是不存在的,这个故事也是我编的。这样特别好玩,因为在某一阶段,我不太满足于虚构这样一个故事,我觉得没什么意思。但如果它是一个被虚构之人写出来的实在的书的话,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新京报:你已经不满足于单纯讲故事的那种虚构方式?
路内:在某一阶段。后来仔细想想我心理上出了什么问题:我有可能是想要抛弃既往作为作家的路内,想与那个身份割席、割裂,投身到另一个身份中间去写作。会不会更好一点?沉溺在既往那个成名作家的身份里,是不是已经使你的小说写作走进了一个死胡同?也未可知,有这样的可能。
新京报:能否具体说说这两种身份在写作上的不同?
路内:写《雾行者》影响了我一段时间,它写到文学青年,写到一种写作的最原初的状态,写《少年巴比伦》和《追随她的旅程》的时候,我都经历了这种状态,因为我写《追随她的旅程》的时候,《少年巴比伦》还没有出版,甚至还没有发表。
我们可以通俗地称这种状态是一个文学青年的状态,我不认为这是完全的文学青年状态,但可以这么通称。这种写作是没有目的性的写作,用北京人的说法,自嗨嘛,他想完成一个作品,对于世界没有太多企图,没有太多文学野心。中国文学所谓的世俗功利心和文学野心,以前是分开的,现在已经变得纠缠在一起,界限变得有点模糊了,本来它应该是界限分明的。
我挺怀念那个时候的写作状态,那两本书加起来也有40万字。但越写你感觉自己身上越背负着一个小说家的声名。有时候有些读者都不喊你路内,喊你路小路,读者跟你说你一定要写路小路,这个人物似乎是你唯一创造出来的人物,似乎你也只有能力在那里面徘徊。评论界和媒体一会儿叫你青春作家,一会儿叫你工厂作家,你也不知道这么矛盾的两个东西怎么会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我想把这些都割裂掉,以另一种身份来写。所以当时悦然找我参加“匿名作家”,我说行,就把名字盖掉以另外一种身份来写。悦然当时提了一个要求是你必须改变自己的风格,我说这不是废话吗?我要拿自己的风格来写个长篇的话,谁都能认得出是我。确实,我完全改变了自己的风格,至少在当时应该没有人知道《巨猿》是我写的,我没作
弊。
采写/新京报特约记者 聂丽平
社会新闻精选:
- 2024年04月26日 21:52:15
- 2024年04月26日 15:59:17
- 2024年04月26日 09:42:57
- 2024年04月26日 09:32:32
- 2024年04月26日 09:22:22
- 2024年04月26日 09:05:21
- 2024年04月25日 20:52:42
- 2024年04月25日 17:03:50
- 2024年04月25日 15:16:47
- 2024年04月25日 14:3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