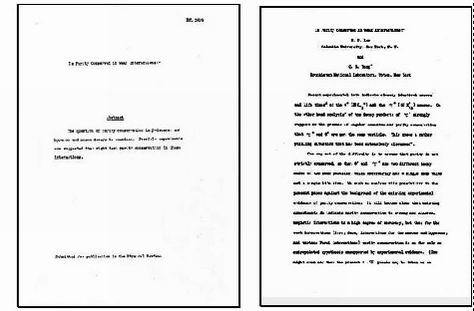- 杨振宁回应“杨李决裂”:《李政道传》有不实之处(3)
VI.
在《1983杨》的29-30页我曾描述1956年5月底前后我怎样写了初稿,打字后成为Brookhaven的2819文件(图三),于6月22日投稿到Physical Review,此原稿当还在Brookhaven和Physical Review期刊的档案中,可以复查的。可是多年后在《2004解谜》23-24页上却说初稿是李在哥伦比亚大学写的;《2010李传》107页也持此说法。哪一种说法正确呢?手头没有文献以百分之百的可信度来回答此问题。可是有一个旁证:李于看到我的这本《1983杨》以后,出版了回应的《1986李》,题目是“BrokenParity”。(此文的中译本见《2004解谜》233-251页)文章对我在这本书中所说的文稿主要是由杨执笔的说法未提任何异议。
如果初稿是他写的,他在这篇他一生极重要的响应文章中会不提异议吗?
VII.
《2004解谜》中说:
“1956年4月初我(李)做出了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以后,到5月份杨振宁才参加进来和我一起对宇称不守恒做了系统性的理论分析工作,一起写出了获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问答(3),16-17页]
“我正在计算和分析。杨振宁要求和我合作,愿意帮助我一起研究。我接受了他的要求。”[问答(8),38页]
这些话显然是要表明,在宇称不守恒的工作上,李是主要的,我只不过是跟随的副手。
这个说法奇怪的颠倒了主从关系,与当时同行们的印象正相反。铁证如下:
在1956年12月初,我们那篇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文章已经发表了,吴健雄的实验正在进行中,但尚无结果。当时在求解θ-τ谜团这个重大问题的战场上,疑云满布,和我们竞争的劲敌是极有名的Gell-Mann(后来于196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以为我们的文章有错误,就匆匆忙忙写了一篇短文寄给我(图四);显然,Gell-Mann以为发现了我们的弱点,所以投下了“战书”(但几天后他就发现我们的文章其实并没有错,又来信取消了他的短文)。
他这封信很值得注意的有下面两点:(1)在短文第一页右上方Gell-Mann写道“佛兰克杨:请于此文送印前告诉我你的意见。”很明显,他知道他的真正对手是谁。(2)虽然我们的文章已发表,排名顺序为李-杨,可是Gell-Mann在全文中只引用杨-李,而从不用李-杨,这就有力地说明了,在他心目中李和我之间的合作关系是怎样一回事。
VIII.
李和我1962年决裂以后,是谁先在公众场合讨论宇称不守恒研究的经过,是谁先引起公开争端的呢?《2010李传》和《2004解谜》都指责我,说是《1983杨》一书起的头。这不是事实。
事实是这样的。1968-1971年间李在多处作关于弱相互作用的历史的演讲,包括在意大利的Erice、CERN、哥伦比亚大学、Rutgers大学等各处。许多听过他的演讲的人告诉我,他基本上是说宇称不守恒的工作是由他开始和主持,中间要找人帮忙计算,就找了我。听后我当然感到震惊与愤怒,可是由于没有见到出版的文献,所以并没有作任何公开响应。直到十年后,我偶然在一本1971年出版的书中,看到了李1970年在西西里岛Erice的International School of Sub-nuclear Physics的演讲(即《1971李》),才了解传言并非虚构。这样,我才在1983年出版的《杨振宁论文选集》(即《1983杨》)中第一次作公开响应。
因此,李1968-1971年所作的许多演讲,以及其中的Erice讲稿的出版,才是我们之间所有公开论争的源头。
那么,李在Erice到底讲了些什么呢?根据公开出版的《1971李》,他演讲的题目是“弱相互作用的历史”,全文共分三节,第二节讲的是θ-τ谜,其中最关键的一段,下面称为(a):
“那时,宇称算符P的真实含义还不清楚,至少对我(李)来说是这样。当然,我了解它的数学特征:P应由一个希尔伯特空间中的么正算符来表示,而在P的作用下,例如对于自旋为1/2的费米场,我们可以得到
等等。我假设,β衰变可用一个更加普遍的拉氏量来描述,它包括10项耦合常数,即通常的5项Ci(i=S,P,V,A,T)以及另外5项宇称破缺常数C'i。随后我从吴健雄那里借到一本由齐格班(K.Siegbahn)编的有关β衰变的权威著作,和杨振宁一起系统地计算了所有可能的宇称破缺的效应。”(此中译文见《2004解谜》,参考文献143-144页。原文没有底线。)
这段文字的含意很明显:观念上的探索、进展都是由李主导,李带着杨做研究,杨的贡献只是做了些计算而已。
因此我知道我不能再沉默,于是在《1983杨》这本论文集中写下了一些我们多年来合作的细节,并写下了下面的一段话:
“一直到今天,我在公众场合都严守自律,绝对不讨论我和李合作的细节。除了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孩子们和两个亲密的朋友以外,我从来没有向外人谈过上文(56h)所述的研究经过。此经过是根据我1956年及1962年的简单笔记而写的。本来我并不准备于任何时候发表这些细节,可是1979年的一天我偶然看见了A.Zichichi所编辑的书Elementary Processes at High Energy,Proceedings of the 1970 Majorana School(Academic Press,1971)里面的李政道的文章,才使得我改变了这个长期以来的决定。在这本书里,李的文章题目为〈弱相互作用的历史〉,其中他描述了一些涉及1949年我们合作的一篇文章与1956年我们合作的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文章的细节。李的这篇文章隐示和暗含了(implied and insinuated)许多事情,关于他和我的关系、关于宇称不守恒的工作,与关于β衰变怎么搞进了θ-τ谜。全文没有讲关键的观念与战略是怎样产生与发展的,也没有讲宇称不守恒文章是怎样写出来的。我于1979年看了这篇文章以后,了解到我一定要在适当的场合把真相写出来。”(译自《1983杨》,30页)
为了回应,李发表了《1986李》。其题目是“破缺的宇称”。此文中译见《2004解谜》,参考文献233-251页。这一次有了一些细节,譬如提到了上面V节中的转折点1与2(改研究β衰变与引入C与C')。而最关键的是其中的一段,下面称为(b):
“那时,杨和我对宇称算符P的实质意义都还不清楚。当然,我们知道它的数学特征:P应当由在希尔伯特空间里的一个么正算符来表示,在P作用下,对自旋为1/2的费米场,可以得到
等等。没有宇称守恒,β衰变应该用一个推广的拉格朗日函数来描述,包括十个耦合常数,常用的五个是Ci=(i=S,P,V,A,T)以及另外五个宇称破坏的常数C′i。
杨和我开始系统地用推广的宇称不守恒作用对所有已知的β衰变现象进行研究。我们很快读完了齐格班的书,经常保持电话联系。我们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完成了全部的β衰变分析。”(此中译文见《2004解谜》,参考文献242-243页。)
对比(a)与(b),显然是看了《1983杨》以后,李觉悟到十多年前他发表的(a)语气不妥,是大患,于是删掉四个“我”字,略作修改,于1986年发表为(b),希望天下人都不去查阅原版(a)。(可是编者季承不小心,竟把原版(a)与新版(b)都译为中文,印在同一本《2004解谜》中。)
Copyright ©1999-2025 chinanews.com. All Rights Reserved